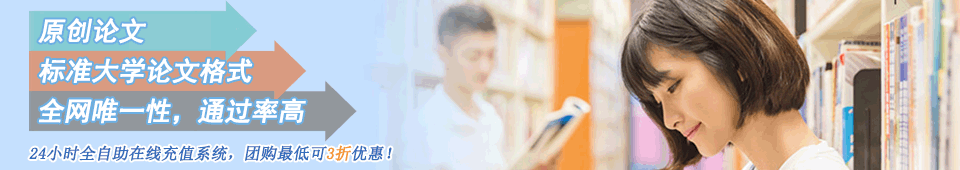(一)《弁而钗》的成书及流传 《弁而钗》,四卷二十回,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评”。作者与评者均不可考,存世仅有笔耕山房刊本,无序,正文卷端题“笔耕山房弁而钗”,有图三十幅,全书分四集,分别冠以“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之名。 《弁而钗》从成书之日起,就注定了其终被禁毁的坎坷命运。我国自古就存在所谓“禁毁小说”,即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中央政权明令禁毁的小说,尤以明清为甚。我国历代小说的禁毁原因,究其根本,都与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再至南宋时毁弃各地刊行的“异说书籍”,统治者禁书的目的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原来的禁毁针对的是直接危害现行统治者的政权稳固,那么销毁“异说书籍”则上升到了强化思想的统一。宋元以来,传统的封建制度及文化愈显疲态,统治者之所以将理学上升为绝对的权威,无非是想改变封建制度与文化的颓势。《金瓶梅》、《痴婆子传》这类艳情小说被禁的主要原因是“诲淫”,即使是《红楼梦》这样为上流社会爱玩鼓掌的抒情式小说也难逃“淫书”二字的指摘,更不用说《弁而钗》这样充满恣意性行为描写的男风小说了。 《弁而钗》,今存笔耕山房刊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及台北博物院。因著重刻露男风,清人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将其列入“更甚而下者”,认为宜“悉当斧碎梨枣,遍取已印行世者,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7]后被列入多种官方的禁书书目之中。关于其版本,现为人知的是日本藏本与郑振铎残本,此两本系同一版本,印制通行时间也较为相近,故两书漫漶不清之处也几乎相同。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刊刻于晚明崇祯年间,晚不迟于明末。 (二)《弁而钗》的内容概述及人物形象分析 “弁”为古时男子穿礼服时所戴之冠;“钗”为古时女子头上所戴之簪,“弁而钗”,顾名思义即是男扮女装、男儿身女儿心之意。全书共四集——“贞”、“侠”、“烈”、“奇”,一集五回构成一个故事,即所谓四记。这四篇故事对待同性恋情皆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学界对同性恋至今仍无权威的定义,其中,张北川教授认为:“在我国现代,在对性伴侣的选择拥有充分自由的条件下,一个性成熟的个体如果具有明显或强烈的指向同性的性欲或同时存有主动的同性性行为方可视之为同性爱者。假如个体仅有偶然的同性性行为,但有关性定向的自我意识模糊,可视为同性性行为而不宜简单地判定其为同性爱者。”[8]性学家李银河则这样说道:“同性恋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9] 相较于异性情爱而言,同性之间的情欲爱恋始终是边缘性的。即使是在“男风”环境相对开明、世人皆通达的明代,许多文学作品与野史都把笔尖瞄准了情色爱欲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题材,这其中男色书写在地位上更为下品,甚至对男色的危害性展开了激烈的探讨,日见关注男性相恋在道德上的沦陷。在这一境况下,《弁而钗》仍能做到始终围绕“情”之一字展开书写,表现“始以情合,终以情全”[10]的意旨实属难得。 弗洛伊德将同性恋分为三类,一是全然倒错的,二是两栖性的倒错者,三是偶尔倒错。以此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同性恋者就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两栖性的倒错者”。弗洛伊德同时又指出两栖性的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这些倒错者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征。”[11]这却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明确地分为两个群体,即主动者与被动者。在同性恋关系中,主动者普遍占有强势的地位,充当男性角色,而被动者处于弱势,充当女性角色。 《弁而钗》中也不例外的出现了女性特征明显的被动者角色,在此之中,又以《情贞记》中的赵王孙与《情奇记》中的李摘凡最为突出。《情贞记》书新科探花林风翔对相貌俊俏的书生赵王孙一见钟情,为能与之诉情,改名换姓入秦春元门下与赵王孙成为同学。时日良多,二人互通情意,情好弥笃。不料二人私情被同窗张狂、杜忌撞破,并四处张扬。赵王孙羞愤欲死,最终与风翔定下北京之约而分手。后赵王孙入京会试,林风翔以原本身份与之再见,二人既是同窗又为座师,同朝为官,至老偕隐。《情奇记》书为解父难自卖其身,入南院做娼妓的少年李摘凡深夜痛哭之声为才人匡时所闻,遭其同情赎身。为报恩情,李摘凡男扮女装嫁入匡家,以姬妾身份随侍。几年后,匡家遭奸人陷害,李摘凡以死保孤,将其养大成人,高中状元。匡时之子为父洗冤,家人重聚之时,李摘凡不辞而别,最终羽化登仙。 《情贞记》开头就明写赵王孙“眉秀而长,眼光而流,发甫垂肩,黑如漆润,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齿白肌莹……虽貌姑仙子不过是也。人及见之,莫道不消魂。”[12]也正是因为如斯美貌,林风翔才会对其一见倾心,“神貌已随之飞越矣”[13],并生出后事。《情奇记》更是把李摘凡塑造成了空有男儿身却彻头彻尾女儿貌的少年郎了,甚至专门写一曲《西江月》咏其美貌,“星星含情美盼,纤纤把臂柔荑;檀口欲语又换迟,新月眉儿更异。面似芙蓉映月,神如秋水湛珠;威仪出洛自稀奇,藐姑仙子降世。”[14] 作者将一个个好读书、有才华的未冠男子描写成女性模样,也正是由于时代所限。不说古代,时至今日,社会传统视角和思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同性恋这一现象无疑是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反抗,尤其是对传统儒家掌握的社会主流思想的反抗。在引入新事物的过程中作者不由自主地加入旧事物的特征以达到更易为人接受的目的也无可厚非,这种“走捷径”的书写使得同性恋被动者更像是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角色,是披着男性外皮的小娘子。 想必作者也意识到了同性恋书写中自身对性别的模糊描写,因此在《情侠记》一记中,一改之前对被动者的女性诱导描写,将一个一身硬气、铁骨铮铮的男儿郎置于被动者设定。其主角张机“臂力过人,能挽铁胎弓,善使方天戟……三百步内,取上将人头,如囊中取物”[15],这样一个男子气概十足的被动者形象置于整个“男风”小说史中,也是少有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弁而钗》四集除《情奇记》李摘凡最后羽化登仙外,其余同性恋者皆为两栖性的,即在维持同性恋情的基础上,又各自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着传统的婚姻生活。不得不说作者对传统思想的“将破未破”的暧昧态度限制了整个文本的价值高度。 与同性恋被动者相对应的主动者形象,作者维持了强势的主流书写。这些主动者,在金钱方面无疑是强势的,这种物质资产给了他们在同性恋关系中维持强势的基础。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强势,给作者想要表达的同性之“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情烈记》中,云汉就曾对文生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与贤弟恩爱极矣,吾欲贤弟不卸女装,取乐一番,可乎?”[16]这种闺房之乐也好,故意狭戏也罢,总之对正面宣扬同性之爱是弊大于利的。 即使作者在同性之间主动者与被动者的形象设定上有一定拘束,但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描绘的情爱关系中,不论是主动者或是被动者,二者双方在人格上体现出了前人未表现出的平等意味。作者借《情贞记》中风翔之口说出:“论情则可男可女,女亦可男,可以由生而死,亦可以自死而之生,局于女男生死之说者,皆非情之至也。”[17]这句话直接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文中主人公对“男风”绝非抱有泄欲、猎奇之意,被动者也并非贪图钱财、权益之辈,双方敢于互诉衷肠并勇于追求,追根究底,也是情由心生,不可自已罢了。 《弁而钗》前两集《情贞记》与《情侠记》的主人公皆为知识分子,不论主动者或被动者。《情贞记》中风翔对赵王孙一见钟情,为亲近心上人,改换身份投入赵王孙师父名下。风翔对赵王孙思慕已久却绝无半点浮气,以至于害了相思病,赵王孙感动于风翔一片痴心才接受了他的情意。二人以同窗身份相交,人格上处于平等地位。作者对这等有情之人,始终保持赞赏与褒扬的态度。《情贞记》中风翔与赵王孙至老弃官偕隐,世世相好不替;《情侠记》中张机与钟图南也双双归隐,子孙世代联姻。这等美好的结局都透露出作者对情比金坚的同性情人的褒扬态度。 《弁而钗》后两集《情烈记》与《情奇记》塑造了两个身份相似却又有别于传统的小官形象。传统的同性恋小说中小官多是唯利是图,WWw.EEelw.cOm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出卖肉体的低下形象。《弁而钗》中出现的两个相似形象——戏子文韵与男妓李摘凡却洁身自爱,博人同情。两人皆出身于书香世家,由于奸人所害沦落风尘,且都在风尘之中秉持本心,品行高洁。两人的地位都很低下,但由于自身知恩图报的性格最终都修成正果,这与以往小说中小官凄惨悲凉的结局大为不同。作者心月主人在《弁而钗》一书中加入鬼神情节,既表达了自身对同性恋的支持态度,又反映出世人对于同性恋矛盾复杂的心态——反感唯利是图的情色交易,提倡真情实感的情爱交流。作者用自己精妙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有情有义、为爱走天涯的正面小官形象。 (三)《弁而钗》中的“情”“欲”交织 明清小说中,有关同性恋的描写大部分是欲大过情,是亵玩,是狭邪,是情与性的悖离。如《龙阳逸史》、《肉蒲团》、《宜香春质》等小说中出现的对男风的描写,都是只有欲念驱使的毫无情感掺杂的低级性描写,读者从中体会不到除了肉欲以外的感情,无法透过“欲”感悟“情”。《弁而钗》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桎梏,他并不回避主人公恋爱中的欲望萌动,但也绝非诲淫导淫,而是把握住灵肉冲突在具体人性形态中的表现形式,让读者的阅读从肉欲交织上升到情感层次,进而了解到所处时代的社会意义。 《弁而钗》出现在晚明这样一个享欲盛行、异端杂出的时代,无法避免沾染上其特有的时代特征,包括对“男风”的不加掩饰的污秽色欲描写,对同性之爱大胆正面的宣扬态度,都表明了作者对传统礼教限制的不满与反抗。但书中又时不时流露出的教化世人的意图又显示出作者道德与心理上的双重矛盾,在道德与欲念中苦苦挣扎的狼狈模样。作者虽然勇于集中且正面地反映“男风”现象,力图提高“男风”的层次,但由于自身不够坚定的书写态度及时代的限制,使得其创作目的并未完全达到。但相较于晚明同期的《龙阳逸史》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宜香春质》,《弁而钗》的正面叙写角度是毋庸置疑的。《弁而钗》尽最大限度讴歌了同为男子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与高洁的品行,为广大读者描绘了一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男风”理想国。 (四)小结 总而言之,《弁而钗》大体上贯彻了作者在文章伊始定下的宗旨——“始以情合,终以情全,大为南风增色。不比那有始者不必有终,完好者不必完情”,从“贞”、“侠”、“烈”、“奇”这四个角度表现了晚明男子同性之间的情意之真、品行之高。 |